引言
一位居于姑射之山的神人,他远离世俗,不食人间烟火,他超乎时空邀游于四海之外。
一句话,他没有任何束缚、不依赖于任何社会的和物质的条件,他是独来独往地存在于宇宙和自然之中的。
而这大概就是庄子心目中“无所待”自由境界的最佳状态。
这样的神人境界,凡人是难以企及的。然而我们也不难看出,庄子的逍遥(自由),实际上更多的是追求心灵和精神的自由。
也就是说,游的主体是人的心灵,而非人的身体行动或实践活动。
庄子自然明白,人不可能靠“吸风饮露”而活着,但庄子却仍言之凿凿。此间道理就在于神人的逍遥凡人是可以通过心的游历、精神的游历去达到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庄子虽极端厌恶和否定现实世界,但却主张“安时处顺”、“和光同尘”、“不谴是非而与世俗处”。
人可以选择死,但是人却不可以选择生,既然自己无力去改变社会,就只有“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人间世》)。
我们不否定这是庄子消极的一面,然而庄子的逍遥游却也恰恰是由此而始。
《应帝王》篇有一段对话,写无名人问天根治天下的方法。
而天根却全不以此为念,反而斥无名人为鄙,怪其扰乱自己的心境。
面对乱世,天根将如何以处?他要与造物者为友,要乘“莽眇之鸟”飞出天地之外,而游于无何有之乡,处在广阔无边的旷野。

身处乱世而不惊,不仅不惊,还能超然于事外、世外,保持自己心境的平静,让心灵和精神轻松闲适无所为地邀游驰骋于幻想的宇宙天地之中,即所谓与天地同游。
这样的人乃庄子所谓的“圣人”、“至人”、“真人”、“神人”,乃真正得道之人。
社会的治乱、个人的荣辱,是均不能进入他的心境的。要到达这样的逍遥境界,庄子以为必须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齐物,即消除以自我为中心的排他性,视万物为一体。
庄子认为,人之所以活得沉重难得逍遥,就在于他们太执迷于生死贵贱、荣辱得失、是非利害这些问题。
要从痛苦中摆脱出来,必须回到无可无不可的淡泊中来。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学会以相对的眼光来看待世间存在的一切事物。
对于事物而言,它们确实有着它们存在的理由和规律,即“物各有性”。
标准总是相对的,在此为标准者,在彼不一定合乎标准,反之亦然。
庄子由此而推论出人类社会的道德是非标准也有其相对性,生与死、贵与贱、荣与辱、得与失,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绝对不可转化的。
“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
在此或此时为贵、为荣、为得者,在彼或彼时就有可能为贱、为辱、为失。没有绝对的标准,焉有绝对的是非?

所以庄子又说,
此就是彼,彼就是此,彼有它的是非,此也有它的是非,彼此如果不以其对立面为对立面,不执于一端,是非两幻,一切矛盾也就可以化解消除。
庄子强调,世间的万物是没有是非、成败的区别的,它们在最终都复归为一个整体。
“达者知通为一”,能体道之人,不会以自身为是去判断事物,因为人只要顺应“物化”,就可破执,就可安于事物无穷的流变,而不会陷自己于变的困窘乃至痛若中而不能拔。
进入逍遥境界的第二个阶段是“吾丧我”、“坐忘”与“心斋”。
这三个概念分别出自《齐物论》、《大宗师》和《人间世》。
“吾丧我”,其意乃完全忘掉自我的存在,不仅要形如槁木,而且要心如死灰,不知自己身之所处,一直到达“身心俱遣,物我兼忘”的境地。
“坐忘”强调要忘掉尘世社会的仁义伦理道德,仅此还不够,还要忘掉自己的形骸心智,只有这样,才能无拘无束,与万物同和。

“心斋”较之前二者似乎要复杂一些,它告诉人们的是当面对纷乱的社会现实时,自我将如何以处。
首先要凝神静气,让自己平静下来;其次对外界的事物不要只用耳目感官去听之视之,看其表面,而要用自己的心智去感受它,看透它的本质。
这还不够,还要用“气”一经过凝神静气之后以一种绝对宁静虚无空明的心境去接纳它,使它也同归于虚无。
因为心智的运用和实际的看透,还是会使自己难以摆脱苦恼,只有用“气”用虚无去对待它,自我才能真正超脱于它而获得精神的快适自由。
可见,“吾丧我”、“坐忘”、“心斋”三者概念虽然不同,论述的角度也不全然一致。
但是,它们的实质却是相通的,都是要使自己忘掉自身的存在和摒弃情感理念等心智活动,让心寂灭。
既无是非荣辱之判断,亦无喜怒哀乐之情感,更无俗人所存有的欲望,处于世而忘于世、不知世。

进入逍遥境界的第三个阶段是无为。对于庄子来说,无为首先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同时,当然也包含着老子以无为治天下的内涵。
在《应帝王》中庄子先从正面描述了无为之人泰氏的生活。
泰氏不受外物牵累(人于非人),所以睡时安稳舒缓,醒时逍遥自适,任人呼自己为马,也任人呼自己为牛,但是却保持着自己内心的真知真情真德。
对这里的“知”、“情”、“德”的理解,当是与庄子的“道”联系在一起的,正如他的“真人”与人的区别样。
接着庄子又从反面描述了“有为”的后果。
南海之帝候和北海之帝忽,以为“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而独待他们甚善的中央之帝浑沌“无有”,于是便“尝试凿之”,然而“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倏和忽并非不是一片好意,但却由于他们不顺应自然而要一味按照自己的心愿去强有所为,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作为一种人生态度,庄子的无为思想有被动消极的一面,它缺乏主动进取的人生精神,但是在强调顺应自然规律的一点上,却仍是值得重视的。
在《养生主》中,庄子虚构了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
在庄子笔下,庖丁已不是普通解牛的屠夫,而是一个好道之人,道者,自然无为也,其体现在解牛中则是不以目遇而以神遇。
庖丁是进入了一种境界,它不仅仅是熟能生巧的问题,而是如何善于利用和顺应自然之道去使自我获得自由的问题,这显然又是不能完全以被动消极视之的。
实质上,从更深层次看,庄子的无为是有所不为而有所为,违反自然的不为,顺应自然的则为之,伤生残性的不为,养生全身的则为之。
所以这才有了“周将处于材与不材之间”的高论。
大木以其不材而得终其天年,雁却以其不材而见杀,两难之间能够逍遥生存十分不易,不“为”可乎?
只是这种“为”不是如良庖割肉、族庖砍骨般去硬碰硬直接面对矛盾,而是要如庖丁顺其自然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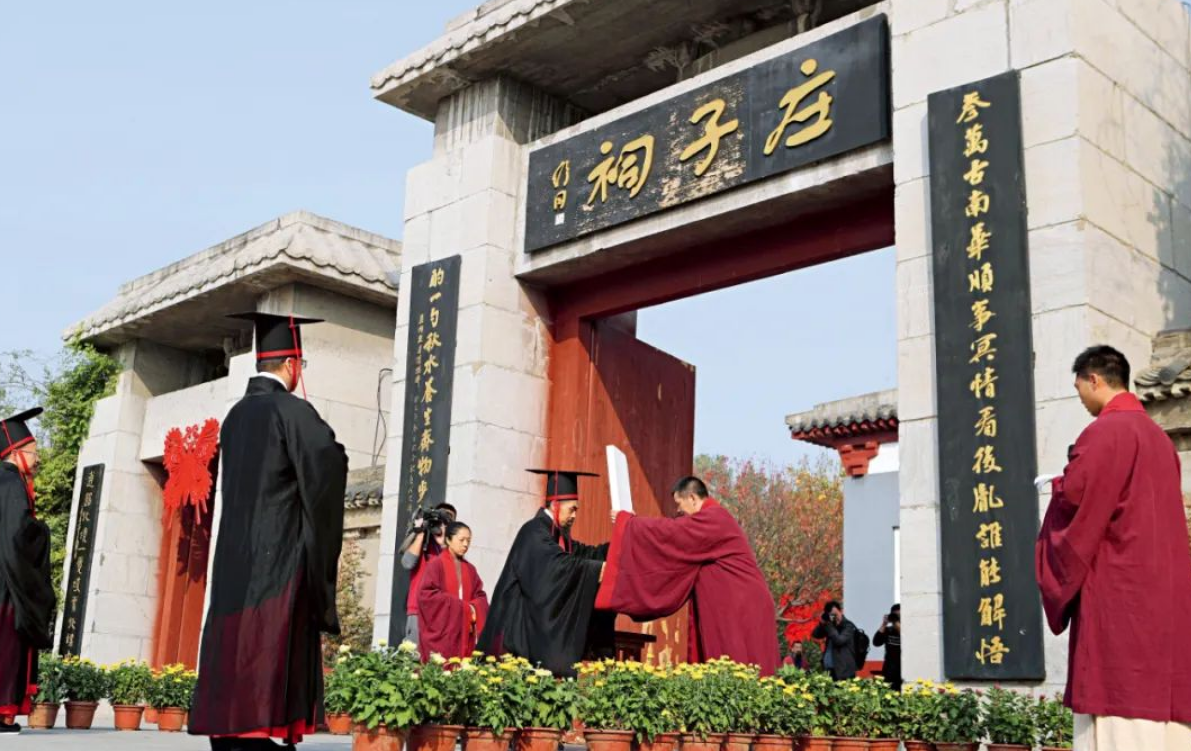
善于回避矛盾,“物物而不物于物”,便可不为物所累,达到逍遥生存的目的。
庄子的无为思想,表现在他的人生实践中便是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和他的不仕和出世。然而庄子的这一治国治世之术在那个社会中是极不合时宜而难以为君王们接受的。
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使庄子感到了“时命大谬也”的不幸。
入世,必然要放弃自己的理想,也必然要以伤生残性为代价,而这与他对自由的追求是大相径庭的。
这样,庄子走向出世便也就无可怪讶。
《达生》篇中“祝宗人说最”的寓言故事,同样诙谐风趣而深刻地表达了庄子不愿出仕、保持自我人格之自由的思想。
由以上分析观之,“无为”是根本,也是目的;而“万物一体”和“吾丧我”、“坐忘”、“心斋”是中介,是方法和手段。
当人内心没有了内外的区别,没有了事物高低贵贱的划分,人便可以一种平静的心境去接受和顺应命运所安排的一切。

当人物我两忘,内心一片空明澄彻,便可超然于物外,邀游于宇宙之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达到灵的永恒。
而这一切当它表现为种具体的生活方式,那就是无为。
无为是逍遥,是自由,是道的代名词。不难看出,庄子的逍遥自由,虽然表达了人类追求精神和心灵解放的愿望和懂景,但是它却带有极大的主观幻想性。
它只向内求之于己,而并不主张通过抗争去获取,因此庄子的自由,只是一种心的造影。
参考文献
1.《庄子》
2.《庄子·内篇·逍遥游第一》
3.《逍遥游》







